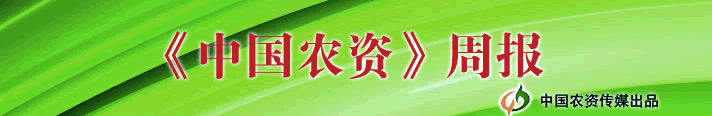我们村以北有一座碾房。
碾房不大,四面是土墙,房顶用瓦盖上,里面有一圈打磨得十分光滑的石槽。石槽的圆心上立有一根木柱作为中柱。碾盘有一米五直径,很圆,像一枚很古老的铜钱。雕作碾盘的石料,来自距我们村以北两公里之外,那地方蕴藏石料,紫红色的。做碾盘的石料,也起自那里,因为用料太大,又不易打炮眼用火药炸,石匠们凭着娴熟的技巧和坚韧的毅力,用锤子和钢钎开采,然后慢慢雕凿加工而成。碾盘运回村里的时候,是很费了一些功夫的。没有大路,只有一条便道,宽不过一米左右,还弯弯曲曲,坑坑洼洼的,村里的壮劳力们就用杠子和铁链去扛,用了一天多时间才将碾盘搬运回来。大人们搬运碾盘的力量让我吃惊。
没有碾米机的时代,碾房里热闹。到了新谷上场的时候,挨家挨户晒好了谷,一袋一袋扛进碾房,按先来后到排了队,等把新谷碾成新米。碾盘这时候也显得很忙,一头性子极慢的水牛拉着碾盘,缓缓地行走,那步伐那节奏很抒情。中柱也随着转,声音吱吱地响。碾盘沉沉的,不紧不慢在石槽里滚动。石槽里的新谷,就这样被碾成了新米,散发着热温和香。我们嘴馋,米一碾好就会趁大人们不注意,偷偷抓把塞进嘴里嚼米硬,一嚼就香。若是大人看见,就说:“小馋猫,吃了生米肚子疼,不能乱吃。”我们听到骂声就逃到一边去,用手捂着嘴笑。其实,我们吃了生米从没有肚子疼过。我们知道大人不让吃,是怕浪费粮食。
碾新米的日子,就是吃新米饭的时节。每户人家的房顶,冒起一缕青烟,饭桌上摆着满甑子的白米饭。吃饭时,下饭菜不用大鱼大肉,只用母亲腌的豆腐和萝卜丝,再加上米汤,就够了,吃起来十分爽口。
村里人逢年过节,也离不开碾盘,尤其是端午节和过老年,母亲就在鸡叫二遍的时候起床,蒸好了饭趁天还没有亮明,把米饭抬到碾房里,用清水把石槽洗干净,然后将冒热气的米饭很均匀地撒在石槽里。米饭是要碾成粑粑,用来做饵块的。碾粑粑费的力气不大,不用水牛拉碾盘,一般只是我和父亲同推。二十分钟就做完了。这时,隔壁邻舍便陆陆续续来了,他们都抬着蒸好的米饭,一家跟着一家排好队。我们离开碾房,走过窄窄的巷道时,还能碰到过往的乡亲。揉饵块要力气大,母亲很少做,通常由父亲做。父亲将粑粑一团一团分开,再一团一团揉成一个一个六寸左右长的椭圆体。这就是饵块。为了不让饵块开裂,保持湿度,母亲就用水保养。饵块在中午或下午吃,做法简单,只需用刀切成丝,放到甑子里蒸熟就行。吃的时候,宰一只鸡煨成汤,用碗盛了,放芫荽、葱、油辣子、味精、酱油,一同拌匀,就可食之。平时我们要吃,就用了另一种吃法,把饵块切成块,放进锅洞,烤得两面焦黄,然后蘸油辣子食之。如果没有碾盘,过节的饮食就没有这样丰富,少了内容。
碾盘是村里人必需的生活工具,只是后来通了电,碾米用碾米机,它的作用才不大了。但是,我们仍然喜欢去推动碾盘,让滚动声震动已经寂寞的碾房。我们或者坐在石槽上,倾听一种旷古的回音,怀想忘不了的历史,追寻原汁原味的生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