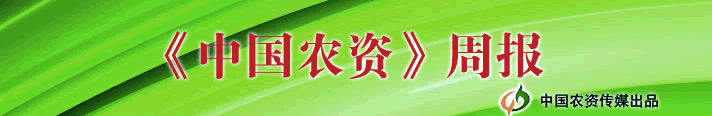和老妈说好周日回家过清明节。
我妈是个急性子。现在她年纪渐大,性子缓和了些,但清明扫墓这样的重要大事,她半个多月前就开始绸缪计划了。周日这天老公临时有事,我开车带孩子回娘家。我开车行驶在再熟悉不过的回娘家的高速公路上,天阴阴的,微微的风,到处是树上新发叶子的嫩绿和油菜花层层叠叠的金黄。广播里播放着毛阿敏的《天之大》。所听所见,让人的心情沉入思念。
到娘家了,叔叔(老妈的老伴)取出小砍刀,准备和我们一起扫墓去。车行两公里,在红山头山脚下停好。叔叔上前开路,挥刀斩草,叫我们要格外小心,可不能踩着尖细的树桩,别让四处扩张生长的枝桠划到脸和眼睛。换口气时抬头望望,这红山头到处一片嫩黄葱绿,笼着一层轻雾薄纱,被雾汽打湿的野草莓的小白花更显精巧单薄。
父亲已经去世整20年了,不知不觉我们到了父亲墓前。现在想来,父亲生前勤奋赚钱养家,但也没有耽误带我们玩耍。暑假里的傍晚,他常骑摩托车带我和弟弟兜风,有段时间常和我们在家唱卡拉OK。他还自制“电瓶捕鱼器”,捞鱼虾非常快,那个暑假,我们家的鱼虾都吃不完。记得有一次,他让我们姐弟俩看他游泳,一个猛子扎进河里,好一会儿不见人影,吓得我和弟弟惊呼大叫。再听到他叫我们名字时,只见他已经站在河对岸的浅滩里。
我小时候特别羡慕有自动伞的小孩。下雨时,按一下弹簧按钮,彩虹色的伞面“砰”地一声被撑开,神气活现。那时我们才从农村到县城不久,我哪有自动伞这样的“洋货”呢?记得一个下雨天,我和父亲出门都没带伞。沿着屋檐往回跑,我这样一路狼狈又兴奋地跑回家。“这个法子不错吧!”他怪得意地对我说。
老照片里的父亲,看上去挺讲究时髦。年轻时的他外形俊朗,穿过两条竖线运动裤和喇叭裤,烫过当时最流行的“费翔头”。那时的老妈很苗条,两根乌黑油亮的大辫子垂到胸前。“我漂亮么?”我曾问父亲。“生气时不漂亮,高高兴兴的就好看。”他说。
父亲还在老家房前屋后种树,其中有不少梨树、水杉。后来我曾跟妈妈说,当时真不该种梨树,因为梨树开白花,又谐音“离”。“老早哪想许多?就是命吧。”20年前的早春,父亲因心梗突然去世。家中长辈们将安葬父亲的墓地选在这处朝向河流、村庄的位置。
老妈一边叫我把花束插在父亲墓碑两边,一边跟我絮叨如今的家长里短。她领着我在墓前磕头,我在心里念着“父亲保佑我们平平安安”。我们早已从失去父亲的哀痛里走出,习惯了没有父亲的生活。母亲拉扯我和弟弟长大,帮我们成家立业,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。
我们扫墓祭祀的时候,叔叔忙着砍去父亲墓四周的杂树、藤蔓,又去附近竹林里挖竹笋。“叔叔人真好!”我对老妈说。“是的!”她回应我。下山路上,她对我说,二姨昨日忙活一整天,摘蒿子、碾粉,等我回来做蒿子粑粑。在我的家乡,家家户户在清明节前后都要做这种时令食物。午饭后,天放晴了,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,老妈叫我午睡去,自己扎进厨房,直到把馅满皮薄、咸甜两个口味的蒿子粑粑做好,摊在案板上晾凉后,再分成几份装好,叫我带回铜陵。
表弟十来岁时有次突然问我:“小沐姐,你爸爸呢?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他?”那时,表弟以为我父亲总是在外有事,所以他们才从未见面。我的女儿很小的时候问我:“妈妈,别的小朋友都有外公,为什么我没有?”我告诉她,外公去世了,已经是一位在天堂的先人,他保佑世间的我们平平安安,希望我们“高高兴兴的才漂亮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