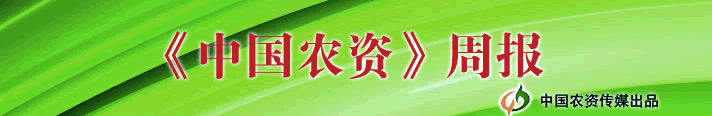童年里的春天,有那么多让我痴迷的东西。
田野里那绿毯般渐行渐浓的野草,山腰上那吸满了雪水叶笣满枝的构皮树,还有那冒出寸许赭红色嫩芽的野刺茏子。放了学,我就和一群伙伴背着背篼往山坡上跑。
想来那样的景色,哪个孩子不迷恋呢?绿毯般的野草里,定睛一瞅,就会发现茎粗叶肥的野葱,扯上几把,白嫩嫩的根须像水洗一般,拿回去掐在老坛酸菜汤里面,甭提有多香。地里那一片腥红色嫩叶的地方就更别提了,肯定是折耳根,挥动锄头从侧边夯下去,轻轻把松土翻过来,一刨一大把,洗净了拌上霉豆腐和辣椒酱,可以下三大碗苞谷面饭!在山腰上将吸饱了汁的构皮叶用镰刀裁下一截,划好印子后用刀柄按在石头上绕着树干轻敲一遍,哗啦啦地树脂连皮一同被剥下来,成喇叭状,用长长的檬子刺别一圈螺旋状,加个哨嘴一吹,“呜-嗷-呜-嗷”,像极了腊月里娶亲的唢呐声。田坎下哪块土角落的嫩刺芽长到了多高多长能不能吃?我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早了嫩芽没有长成吃了可惜,晚了嫩芽长老了嚼不动就不好吃了,因此我们会算约好哪天去采摘。
当然,漫坡跑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大片肥肥的猪草,“猫尾巴”“肥猪苗”“橑子尖”“糯米菜”……几双的眼睛随时都在扫描,看到哪块地里猪草茂盛,几个背篓一哄而上,刷刷地割满背篼,在“呜-嗷-呜-嗷”的构皮喇叭声中,一群小伙伴笑着闹着朝炊烟缭缭的寨里飞去……
春天的阳光,明亮,但不刺眼。沐浴在阳光里,感受着暖洋洋的太阳把每一个毛孔都烤热放大,毛发在棉袄里面伸展,麻痒痒的让人忍不住要解开扣子伸手进去可劲地挠。
春天的声音,热闹,但不嘈杂。嗓门最大,数那春雷。常常在半夜里就“轰-隆隆、轰-隆隆”地响起,仿佛有个大力士在云朵里推动巨大的石磨盘子磨面。
春去春又来,时过境已迁。
这个春天,我想抽空带上孩子,到田埂上感受那扑面而来的春风,去田野里寻找那一片赭红,任他汗湿脸颊,管他泥土满身,随他放肆奔跑。这样的情景,权当是与儿时的小伙伴儿就别重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