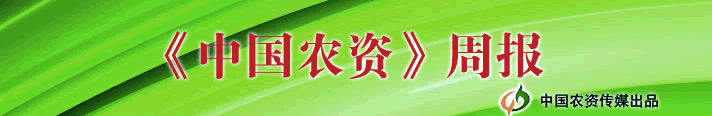那是2005年的年底。眼瞅着就要过年了,但母亲一不留神,居然把骨头摔断了。
出事的那天阳光灿烂。一大早,母亲就急不可耐地把自灌的香肠拿到阳台上晾晒。每年腊月上街称肉灌几十斤香肠是她的习惯。腌好后,平均分配给我们子女三家。怕她累着,我们常劝她不要麻烦了,超市里都能买到。母亲却说街上买的哪有自己灌的实在。我们劝不住,只好由着她。
那天在晾晒香肠的过程中,兴许是手里一次提得多了点,她体力不支,身体失去平衡,一屁股坐在地上。这一坐地,就坐出个盆骨断裂来。母亲住进医院做了换骨手术。
转眼已是农历除夕。医院里能走动的轻病号,几乎都请假回家吃年夜饭去了。从早上开始,病房里就已经空落落的。母亲术后不久,伤口还没拆线,躺在床上不能下地。这个大年夜,她注定要在病房过了。
那年,也是我父亲去世的头一年。母亲又住进了医院。我们几个弟兄一合计,干脆从家里把酒菜带来,跟母亲一道在病房过年算了。母亲说:“那成什么样子,在医院过年不吉利,你们回家吃完年饭,夜里派一个人来陪就行。”我们拗不过,只好遵从。
我和弟弟妹妹们做了分工:他们回家忙年饭,我一人在医院陪母亲。黄昏时分,几瓶输液终于打完。病房外的爆竹声越来越稠密。医院给回不了家的病号送水饺来了。我趁热喂了几个给母亲吃,她却一再催我快点回家,别让弟弟妹妹他们久等。临出门,母亲又叮嘱:“吃饭前记住在家门口给你爸烧几刀草纸,告诉他,今年我不能回家陪他过年了,明年过年再把他接回家团圆。”我的眼睛顿时湿润了。
年饭是在弟弟家吃的。父母不在桌,“团圆饭”吃得很冷清。考虑到晚上还要去医院值夜,我没敢沾白酒。只喝了半瓶花雕,便匆匆忙忙往医院赶。
再到医院,已是晚上七点多。母亲躺在床上看我们特意为她住院买的六英寸小黑白电视。此时,不知是半瓶花雕酒劲上来了,还是这些天伺候母亲有点辛苦疲惫,在屋外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电视屏幕里欢声笑语的伴奏下,没等央视春晚开场,我便靠在旁边的一张空病床上,酣然入梦。
这一觉睡得好沉,醒时,狗年的零点钟声已经敲过。春晚曲终人散,窗外嘈杂的鞭炮声也渐渐稀落。我是被母亲翻动的声响惊醒的。睁眼望去,她正侧着身,趴在床上,低着头,伸长手臂,艰难地够床底下放着的便盆。我一阵懊恼和自责,母亲肯定被尿憋坏了。她白天打了四五瓶点滴啊!我上前掀起床单,只见床底下的尿盆已倾翻,盆里的尿泼了一地。我嗔怪道:你端便盆怎么不叫我一声?母亲说,看你睡得香,我就试着自己够便盆,不小心洒了。
母亲因为输液,这些日子起夜较多,两个小时就要给她端一次便盆。而这一觉,我睡了近六个小时。躺在病床上的母亲,在行动如此不便的情况下,还用自己的方式心疼着儿子。一股温暖和酸楚,潮水般涌遍我全身。
窗外,除夕的烟火还未散尽,早起的人们又放起了开门炮。新的一年开始了。我问母亲,新年有什么愿望。她说,她想早点出院回家,年底还给我们灌香肠。